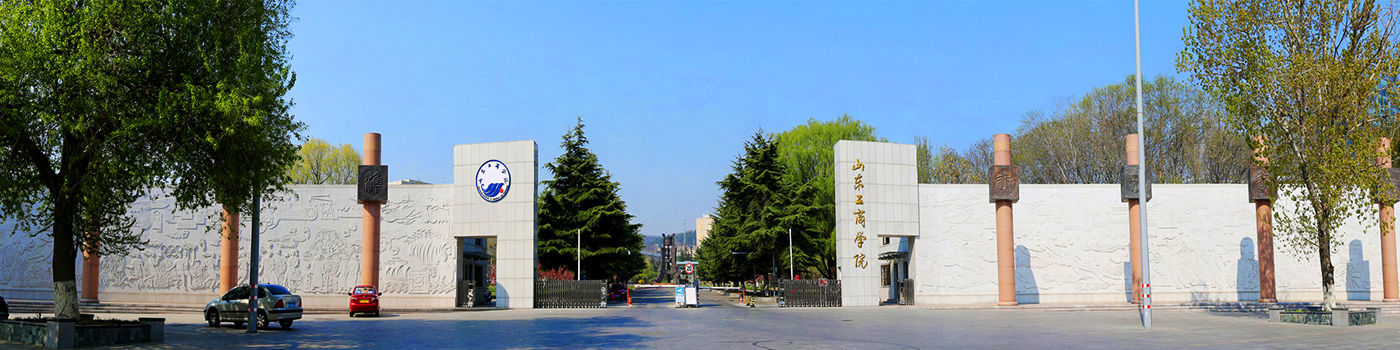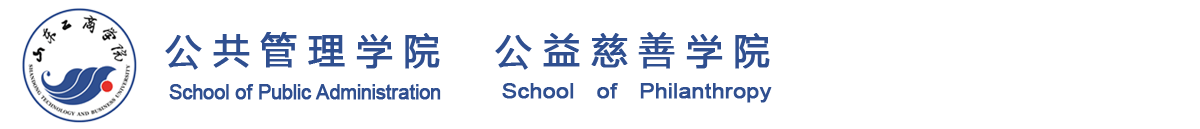诗人北岛曾说:
“父亲是一本书,没有华丽的词句,
却有道不尽的真实。”
一个肩膀,一个背影,
父亲带给我们的安全感,
永远不可替代。
在第114个父亲节暨79个中国父亲节到来之际,
我想对爸爸说:
父亲节快乐,您辛苦了!
你是坚韧的大树
也是温柔的阳光
高尔基说:“父爱是一部震撼心灵的巨著,读懂了他,你也就读懂了人生。”
小时候,他把我托在肩上高高举起,问我:坐飞机有不有趣?上学后,他总是望着我的背影消失在校门口或站台,直到不能再送别了,才将沉甸甸的书包或行李给我。


你的肩膀
一直是我的依靠
《淮南子》曰:“慈父之爱子,非为报也。”
爸爸的手上,有着厚厚的,茧那些茧,见证了岁月。他是饱读诗书的学者,是驰骋商场的战士,是辛勤工作的劳动达人。他用开阔的视野扫视属于你的前路告诉你,大胆向前,不必怕。
父爱这座灯塔,一路指引,一路照亮!


从不把爱挂嘴边
却用行动去诠释对我的爱
《诗经》中说:“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劳瘁。”
在遇到难题时,总在第一时间,寻求爸爸的帮助:取快递、修灯泡、通水管……
爸爸的世界没有“累”字,他好像无所不能,揽下所有的脏活累活,呵护我们温馨的小家。


名家和父亲的回忆录
01
《在燕南园随父亲读书》
从小父亲很少过问我们的事,我们兄弟姐妹多由我母亲来管理,父亲对我们一向慈爱,在我们小时候,他见到我们总是拍拍我们的头,或者抱抱我们。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常常为哄我妹妹一平睡觉,抱着她来回地走,用湖北乡音吟诵着《桃花扇》里的《哀江南》:“山松野草带花桃,猛抬头秣陵到——”如果我们生病,他总是带我们去医院,他不相信中医,虽然我们后院住着一位姓周的中医师。父亲没有什么嗜好,时间多用在写他的书上。
他的休息,一是逛琉璃厂的书店,买一点不太贵的书,二是每一两周都要到中山公园春明馆或来今雨轩和钱穆、蒙文通、熊十力诸位老伯坐茶馆,喝茶聊天。这时候他总是带着我和妹妹,我和妹妹都很喜欢吃那里的包子,父亲给我们买包子吃,然后让我们在公园里自己去玩。到昆明后,一九四四年秋我妹妹一平去世,对我父亲来说是很大打击,因为他最喜欢的就是我的这个妹妹。这样,我们家只剩下我和比我小十岁的弟弟一玄。
一九四五年一月我自重庆回到昆明后,感到他把对我妹妹的慈爱转到我弟弟身上。那时我弟弟才八岁,他喜欢玩一些机械性的东西。在昆明南屏街一带是美国军用剩余物资的集散地。虽然我们因战乱生活很困难,但父亲仍然常带弟弟到南屏街去买一些弟弟喜欢的小机械零件。有时父亲也买一两包美国烟和一两本简装本的英文侦探小说。
父亲对我们的学习很少过问,也很少对我们有什么要求。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他的为人处世受到教育:例如他对吃、穿等等从来就没有什么特殊要求;他从来没有当着孩子们的面说过别人的坏话,也没有在孩子们面前发过脾气;他对我们家的帮工非常有礼貌,而且可以和车夫坐在门槛上聊天;他拒绝傅斯年先生给他兼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平办事处主任的兼职薪金,因他认为既然拿了北大的一份工资,就不应再拿中央研究院的钱:他对伯父汤用彬在抗战期间曾任伪职一直没有原谅等等,可以说对我们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汤一介

02
《背影》
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座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要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只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我现在想想,我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往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儿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力支持,做了许多大事。哪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朱自清

03
《我的父亲冯友兰》
父亲曾提出,大学教育的目的之一,是要让人能够欣赏古往今来美的东西。他本想在完成《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大书以后,写一些艺术感受,题名为《余生札记》,已成一篇《论形象》,从杜甫的《丹青引》谈起,讨论美术创作。可是,《新编》以后的余生很短,他已经泪干丝尽,不得不带着满脑子的“非常可怪之论”远去了。那些发光的“非常可怪之论”,究竟还有多少,内容是什么,能够给人的精神世界增加怎样的活力,永远不能为人所知了。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的遗憾。
父亲的趣味很广泛,对文学艺术有许多见解。他告诉我,昆曲音乐中直起直落的变化,称为“方笔”;北京城里钟楼和鼓楼的气韵不同。他讲过,一位朋友看晚年程砚秋的演出,程一出台,甚显胖大,这位朋友“哎呀”了一声,心想:这怎么受得了!听了几句之后,觉得完全受得了,再听再看,觉得很愿意“受”。这里没有直接称赞程氏的表演艺术,却让人感到程的表演之高超。我们每年春天要去颐和园,看玉兰,看海棠,看桃花。后山的桃花映着松树,又活泼又庄重,是一幅永远难忘的图画,我们常流连在这幅图画中。父亲却不让任何一种趣味成癖,绝不玩物丧志,他离不开的是哲学。
——宗璞

老爸给的关爱
总是满格信号
时光总像是无情的,
不顾你的意愿,
就推着人向前走。
常常感慨,一年一年过得真快,
怕还来不及扛起生活的重担,
怕时间流逝的太快、太急,
怕我或您、您们留有遗憾,
更怕,您的遗憾会与我有关。
今天,在属于您的节日里,
祝您节日快乐!
希望您永远健康、永远平安!